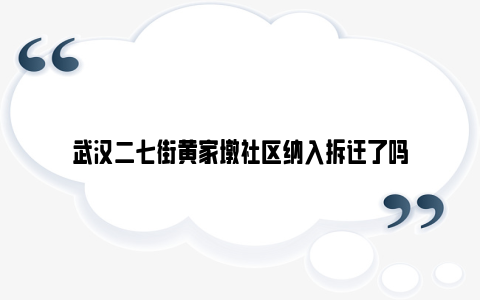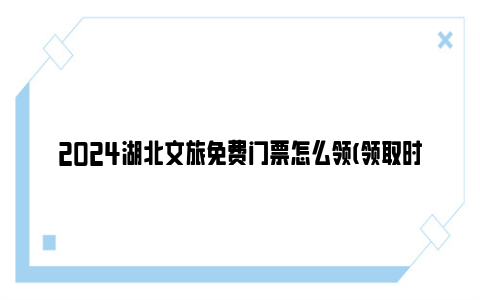新中国成立后,我曾4次到过武汉。这座雄伟的江城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,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我第一次去武汉是1951年10月。那年,我和香玉剧社的同志们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,为捐献一架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正义战争巡回义演。
到达武汉的次日,中南文联、湖北省文联在汉口人民剧场特为我们举行了欢迎茶会,省、市文艺界的许多名流都出席联欢,陈伯华、沈云陔、言慧珠几位戏曲界的大家。他们不仅热情致词,而且都表演了自己的拿手唱段。

捐献演出的地点是在老汉口车站附近的人民剧场,我主演的剧目主要是《花木兰》、《拷红》、《如姬窃符》,此外,还有赵义庭、李兰菊等主演的《邵巧云》、《南阳关》、《黄鹤楼》等。观众们出于对捐献义演的热情支持前几天的戏票早已“抢购”一空。演出时,剧场里的气氛十分热烈,那时还没有字幕,我的演唱经常是掌声不断。演完戏,许多观众还久久不肯离去。武汉观众的爱国热情,他们对捐献义举的拥戴,使我深受鼓舞。
在武汉演出的14天,票价比开封、郑州、新乡订得高,收入很好。
第二次来到武汉是1956年9月下旬,此时,香玉剧社已改建为河南豫剧院一团。作为正常的出省艺术交流,我们的演出地点仍在汉口人民剧场。这次到武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武汉长江大桥正在建设中,武汉市文化局特意安排我们全团同志前往参观。正在修建中的长江大桥,是那样的雄伟壮观,那样的气势磅礴,滔滔的江水在桥下奔涌而去,它却巍然屹立,稳如泰山。
这一次演出,因为有1951年奠定的基础,仍然很热烈。剧场每天均告客满。就在此时,我排出上演了经过改编的豫剧传统戏《桃花庵》,得到了武汉方面领导、专家提出的宝贵的修改意见。
又过了5年,我和河南豫剧院一团的同志们在深圳为过境的香港同胞公演后,经韶关又来到阔别已久的武汉。此时,江城进入炎热的夏季,我们住在位于武昌的湖北省政府招待所,演出地点就在闻名遐迩的洪山大礼堂。60年代初,尚无空调设备,剧场的同志特为我们在舞台两侧摆上冰块,即便如此,我穿上戏装,仍然是挥汗如雨。看到皮革软座上坐无虚席的观众,我们激情似火,可观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更火……午夜散戏,我们乘车返回住地,看到马路两侧的人行道上,或坐或躺,全是乘凉的人群。生存在这里的人民的坚韧与耐力,使我油然为之钦佩。
1987年,我又一次来到阔别16年之久的武汉,此时我已是发染霜雪的64岁的老人。这年9月,首届中国艺术节中南区分会场设在武汉市,文化部特别安排几位老艺术家作专场表演。可能是一种缘份,我们演出的地点仍在汉口的人民剧场。在这里,刻画人物入木三分的陈伯华演出了名剧《宇宙锋》;已年逾花甲,但宝刀不老、风采不减当年的尹羲演出了《拾玉镯》;以声腔艺术闻名于海内外的粤剧旦行中的泰斗红线女,献演了包括《搜书院》、《关汉卿》一些名段;湘剧名家谭保成演出的《醉打山门》以人物的形神兼备、舞姿的独具一格而为观众所称道。而我演出的节目是3段豫剧清唱。令我感动的是,武汉观众以有节奏的掌声,甚至伴以跺脚,要我多次谢幕,以此来表达对我的热情。那两场演出的热烈的效果,是很少见的。
艺术节闭幕时,大会组委会奖给我一尊“香玉杯”。回到郑州,我和老伴陈宪章商议,“好花不常开,好景不常在”,艺术总要后继有人,“薪火”总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,干脆把“香玉杯”作为一种常设奖项,奖励基金由我自己筹集,奖励从事河南地方戏曲各个专业的优秀人才。已历时11个春秋的“香玉杯艺术奖”的设立,源起于我在武汉的演出。武汉人民多年来对我的支持与鼓励,使我永生难忘。
由于年事已高,青春不再,我在舞台上出现的机会越来越少,加以患有膝关节骨质疏松症,血压也不稳定,行动不便,我也减少了外出的次数,至今,又是11年未去武汉。我想,这些年来武汉的变化必定很大,它在改革开放年代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定是令人振奋的。如果健康状况许可,有朝一日,我会重访武汉,看看江城的新貌,和众多的亲爱的观众再次见面。
原创文章,作者:nbdnews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nbdnews.cn/07/16/16/29456.html